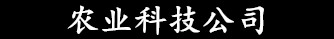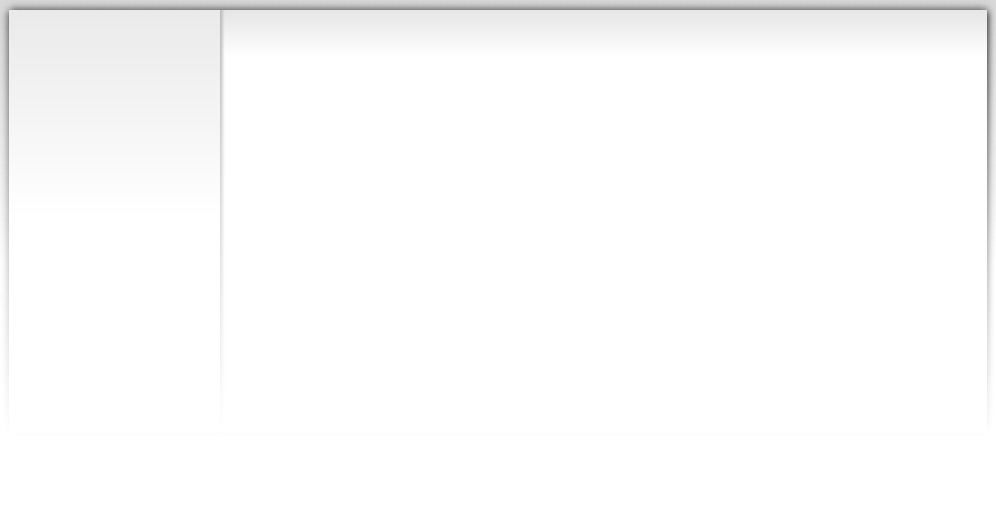
{富途平台}数据报告:测试招商,暑假将至之时,开始制定暑期旅行计划的爸妈们发现,不少适合溜娃的网红农场纷纷关闭整改,加上之前成都天府绿道10.1万亩耕地“复耕还田”的新闻闹得沸沸扬扬,大面积的绿地转为耕种用地,让人不禁发出疑问:
今年以来,我国部分地区确实对违规占用耕地种树造林、挖湖造景等现象进行了纠偏,要求恢复种粮,但新华社日前撰文指出,这并不是“退林还耕”,它的准确叫法,是“整改复耕”。
毕竟,农业毫无疑问是国民经济的基础,“民以食为天”,保护好耕地,让我们的良田实现高质量发展,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。
粮食短缺是当今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,极端天气、局部战争冲突、公共卫生健康突发事件等也都可能对城市的粮食安全造成威胁。
学者温铁军先生曾在一次讲话中提出,“都市农业”是我国生态发展的特色道路。
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和微生物学教授迪克逊·德斯帕米尔(Dickson Despommier)也提出过这样的观点:如果世界上每个城市都在室内生产10%的食物,那么每年就可以使34000平方米的土地回归森林。
在人口密度很高的大都市中,“屋顶种菜”成为都市农田的理想选择,也成为一种改善自然环境,让都市人解压的重要生活方式。
巴黎市长Anne Hidalgo在法国首都开设了城市屋顶农场,该项目旨在通过利用建筑屋顶来种植蔬菜,为城市带来更多绿地,巴黎的城市农场大约有14000平方米,可种植30多种不同种类的植物,将使用有机耕作方法。
2019年,新加坡首个组屋社区停车场屋顶农场建成,占地1800平方米,屋顶农场利用独创的“水-有机系统”,在垂直的铝制种植塔中,种植有机生菜、芥蓝等蔬菜。一年之内,该农场共收获了18吨蔬菜,对附近居民的蔬菜需求是极大的补给。组织方还会招聘附近的老年居民,加入种植工作中,也为这一群体带来了再就业机会。
在泰国曼谷国立法政大学的屋顶,“亚洲最大的城市屋顶农场”2020年刚刚落成,面积达到22000㎡。屋顶农场中最亮眼的是一片水稻田,农场构造结合了传统梯田的土方结构,雨水顺着斜坡流下,滋养着农作物,同时过量的雨水可以被收集起来。屋顶还装有太阳能电池板,产生的电能可以用于灌溉农场和为校园建筑供电。
在深圳,也已建成360多个“共建花园”,南山区城中村的一座公寓楼的屋顶,便是其中之一。公寓楼共6层,经改造后可提供300间出租房,住户多数是年轻人,这片小农田采取“责任田”制,由种植箱组成,每户都可以认领自己的种植箱,青年公寓的管理团队负责基础维护。
深圳城中村屋顶“南园绿云”共建花园的“云田”(图源:十一建筑设计事务所)
越南知名的武重义建筑事务所设计建造的一座幼儿园,像是一大片绿地上的一个三连环的结,草木在这些高低起伏的环形中生长,幼儿园的屋顶上铺有草坪,种植了植物、蔬菜,小朋友们既可以在草地上自在地奔跑、游戏,又能参与种菜等活动,体验和学习农业种植技术。
让摩天大楼变成“垂直农场”,是实现“在更少的土地上生产更多作物”的思路之一。
“垂直农场”的概念,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迪克逊·德斯帕米尔(Dickson Despommier)于2000年提出,在他的构想中,一幢30层的摩天大楼能够养活5万纽约曼哈顿区的居民,如果有160座这样的建筑物,就能为所有纽约市民提供全年的粮食。
近年来,得益于水培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,通过摩天大楼立面上获取太阳能量,并将其变成一个巨大的农场,已经成为可能。
新加坡的SKY GREENS是最成功垂直农场之一。农场是模块化结构,框架用铝和钢制成,坚固耐用,高度可定制和扩展,可以适应土壤种植或水培等不同的栽培方式和自然条件。
由BIG建筑事务所与CRA-Carlo Ratti Associati联合设计的280米高的金凯源中心(CapitaSpring)大楼,是目前新加坡最高的“垂直农场”。贯穿建筑表皮的平行线条向上延伸,流线型的建筑立面充满了动感,绿植从内部向外探出,为整个建筑带来生机与活力。
大楼中有五个不同的主题花园:新加坡美食遗产花园、健康花园、地中海花园、澳大利亚花园和日本花园,农场种植的蔬菜和香料将供给楼内的餐厅使用。
建筑师斯坦法诺·博埃里这些年一直在进行“城市垂直森林”的实践。现在,他已经将“垂直森林”升级成了“垂直农场”。
在上海光明城市垂直农场的方案中,博埃里建筑设计事务所首次将“垂直森林概念”与“农场概念”结合在一起,在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的设计中,建筑物阳台上所种植的植被主要是蔬果类和可食作物。
塔楼上设计了12个“绿色泡泡”作为温室,以确保植被的健康生长,独家研发的温室系统可以保证垂直农场中植物的健康生长,确保建筑内农业生产、工作、生活等活动的进行。
“垂直森林”式的农场也会遇到很多现实中的问题,比如植被缺少打理导致蚊虫聚集,遮蔽采光,甚至植物高空坠落等。
卡洛拉蒂设计事务所为深圳设计的一座“垂直农场”则试图解决这些问题,共51层高的大楼,每层边界上都可以种植食物,仅一个摩天大楼就可以生产成千上万人的食物,植物位于建筑物“双层表皮”的两组窗户之间,日常维护工作由人工智能机器人来完成。
如今,有一批社区型的城市农场开始流行起来,为城市补充粮食蔬菜,也传递给市民们“绿色生活”的理念。
中国香港的K-Farm由一个非政府组织经营,是全香港第一个结合了水耕、鱼菜共生、有机耕种的社区农场,农场占地2000平方米,设有水培池、垂直农场装置、防雨棚、有机农场和一个漂亮的十二边形钢结构温室,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袖珍公园,市民们争做农夫,通过参加种植班、租种植箱的方式参与其中。
美国费城市中心市政厅的对面有一个叫Thomas Paine Plaza的广场,也被改建为生态农场,人们可以坐在广场中,边享受咖啡美食边看农作物一天天长大,这些农作物会提供给附近的餐厅,并帮助有需要的人们获得健康食品。
农场的设计采用鹦鹉螺形状,围绕着巨型游戏雕塑旋转,仿佛正在向城市伸出双臂。
浙江杭州八卦田遗址公园,曾是南宋皇家籍田的遗址,改造后成为一个展现农耕文化的农业科普园地和历史文化遗址公园,恢复了南宋时期皇帝躬耕劝农的自然风貌,农田保留了农业生产功能,成为开放给市民的公共公园设施。
同济大学景观系教授刘悦来带领“四叶草堂”团队在上海建了200多个社区花园,其中也有不少是农园和种菜区,居民志愿者都会参与种植活动,这些“微农场”已经变成了集科研、农业生产、社区活动、教育娱乐于一身的新型城市公共空间。
城市就算是没有绿地条件,也可以拥有农场。由挪威建筑师Andreas Tjeldflaat创立的Framlab,设计了模块化的“城市农场”,提供了可自我调节的垂直农业结构,可以为附近社区提供当地农产品。
在城市中建立农场,是可以让城市在食品上自给自足的最佳方案之一,而城市农场,也可以明显缓解“热岛效应”,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日益严峻的气候问题。
可喜的是,在今天的城市中,大到几十亩的绿地式农业空间,小到密集住宅区屋顶上的一个种植箱,城市农业正在星星点点地连成一片。
不久的将来,也许在城市的大厦里、办公室里和家里,都会有农场,耕种与城市生活的距离在一步步拉近,我们不用去乡村,就能找到诗和远方。
相信建筑师们的积极实践,会在未来让食品的生产与供应发生巨大的变化,改变未来世界的面貌。
《“水稻上山”引争议,全国农技中心回应》(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,作者:房宁、韩浈浈)
《水泥森林中如何植入田园风光?中外12座都市农场让人们回归自然》(景观周)